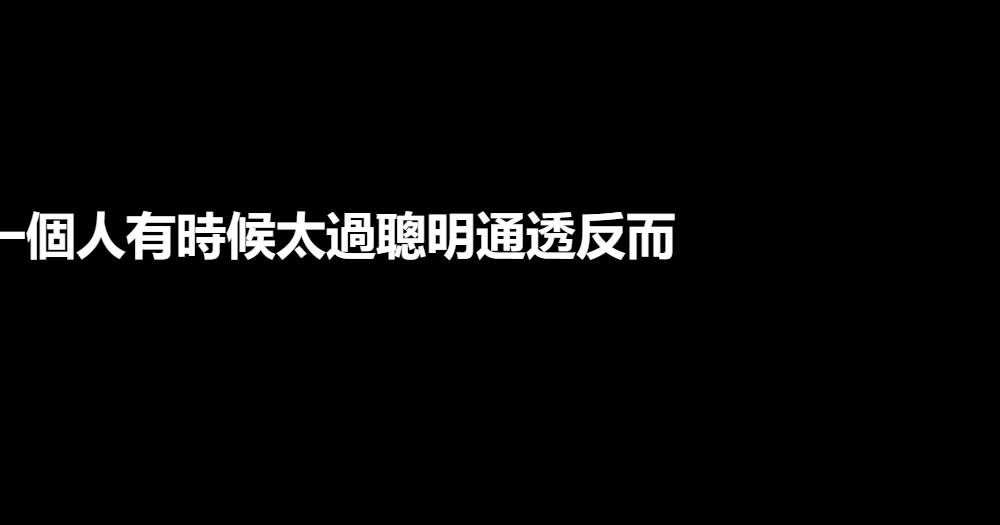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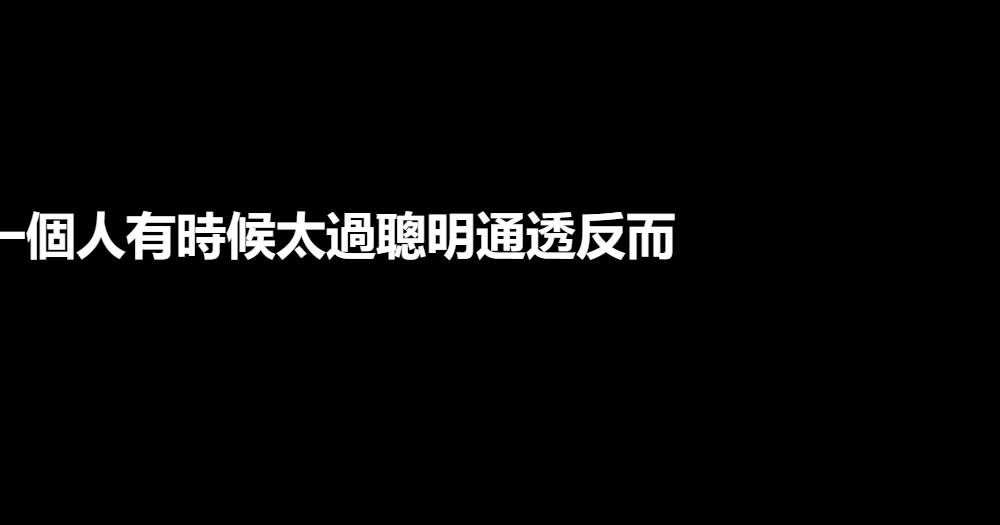
我在百度地圖的街景里,看到了我去世多年的外婆。
她的脖子上沒有傷疤,也沒有四濺的鮮血。
盛夏的陽光照在她身上,她穿著那件洗到發白的淡藍色上衣,像是從不曾離開我。
屏幕下方標注的時間是2015年,8年前的夏天,她還沒有被殘忍地割喉。
我的眼淚頓時就掉了下來。
外婆,原來我們已經分別那麼久了。
外婆,你本來應該長命百歲的。
……
在2015年的那個秋天之前,我認為世界很美好。
我和外婆居住在筒子樓里,周圍都是熟悉的街坊鄰居。
我們夏天在小巷里乘涼,冬天一起拖著椅子出門曬太陽。
偶爾有大爺組局下象棋,外婆會湊過去看。
盡管她并不懂,但是她愛湊熱鬧。
我們生活的環境,看上去就是這樣寧靜又祥和。
直到那個夜晚——
我像往常那樣下了晚自習,在一個十字路口處跟好朋友道別。
她往左邊走,我則直行。
書包沉甸甸的,壓得我肩膀疼。
路燈忽然閃了幾下,然后就徹底變黑。
我嚇一跳,一腳踩空,踩到了積水坑。
我慌亂地伸手去扶墻壁,卻感到有人從身后抱住我,將我往后拖。
我奮力掙脫,尖叫起來:“救命啊!救命啊!”
他騰出一只手,死死捂住了我的嘴巴。
整棟樓都是黑漆漆的,沒有人應答。
我想起來了,市政府出台電影惠民政策,我們小區,正好拿到了今天晚上的免費電影票。
有狗叫聲接連響起,卻止步于防盜門,沖也沖不出來。
身后禁錮我的力量更大了,仿佛鐵鉗,我再怎麼掙扎也掙不開。
脖子和臉頰火辣辣的疼,腰側的衣服被扯了起來,他把一塊布塞進了我的嘴里。
然后,他扯開了我的校服襯衫。
我瘋狂掙扎,帶著一排自行車往下倒。
嘩啦啦的,在黑夜里發出劇烈的響聲。
一輛自行車砸在了他的背上,他的動作一頓。
我借機起身瘋狂跑開,沒跑出幾步路,就被他一腳踹在腿彎。
然后,被他拽著頭發拖了回去。
狗叫聲更為狂亂,小巷外有車子經過的呼嘯聲,有市中心煙花升空的聲音。
完全地,將我細碎的掙扎聲淹沒。
那男人戴著口罩,戴著帽子,一片混亂中,我伸出手抓他的臉——
口罩掉了。
竟然是樓上的叔叔。
月光清亮,他的眼神有一絲慌亂,下意識重新把口罩拉上去。
我嘴巴被堵住,說不出話,只能乞求地看著他。
叔叔,為什麼要這樣對我。
叔叔,明明你也有女兒啊。
他盯著我泛紅的眼角,那絲慌亂很快變成了狠戾。
然后,他暴躁地解開皮帶,一把扯下我的校服褲子。
有腳步聲響起。
手電筒雪亮的一束光,搖搖晃晃著向我們走來。
我聽見了外婆的聲音。
“言言怎麼還沒到家啊?”
鄰居叔叔猛然停住,像拖死狗那樣,把我拖到了車棚的陰暗處。
我的四肢都被鉗住,淚水瘋狂涌出。
我拼命掙扎,整個人被他死死箍緊,動彈不得。
我嗚咽著,試圖用喉嚨發聲。
可那聲音太細微了,被一簇簇的煙花升空聲淹沒。
外婆站在小巷口,抬起頭,看著天邊的煙花。
那絢爛的光影,如流沙般傾瀉而下,在天邊綻放出極燦爛的光彩。
而我被樓上的叔叔抵在狹小的車棚里,耳邊是他粗重的喘息聲,后背是令人發麻的炙熱。
煙花停了。
外婆收回了目光,在巷口坐下,等著我放學回來。
我瘋了一樣掙扎起來,手肘撞到了他的胸膛,他悶哼一聲。
我用盡全力尖叫,聲音被抹布堵住,大腦都快缺氧了,卻只能發出一點點恐懼的嘶啞聲音。
可是外婆沒有聽見。
她只是翻出老年機,撳了幾個按鍵,像是在看時間。
“這孩子……”
又過了片刻,她慢悠悠地往回走。
雪亮的手電光幾次快要照到我所在的角落,她卻始終沒有看見。
她即將與我擦肩而過。
淚水瘋狂地掉落,我嗚咽著,掙扎著,然后被鄰居叔叔掐住了脖子。
呼吸完全被剝奪。
眼前出現了無數顆金星。
下一秒,外婆對著手機大吼:“我家在保松小區7棟!門口的自行車棚里!有人要強奸我外孫女!”
身后的桎梏猛然一松。
我跳起來逃跑。
校服褲子絆住了我的腿。
我摔在了地上。
書包里的東西散落一地,露出花花綠綠的小玩意兒。
飯卡、小鏡子、公交卡……水果刀。
與此同時鄰居叔叔也追了上來,扼住我的喉嚨,兜頭一耳光扇了下來。
外婆蹣跚地沖了上來,拿著手電筒,一下一下砸著他。
“言言,跑!”
外婆被一把搡到了地上,頭撞在了自行車棚的支架上,發出一聲沉悶的鈍響。
好一會兒,也沒有爬起來。
我聽見她微弱的聲音:“言言,跑啊,跑……”
叔叔松開我,站起身,沖著她走過去。
他很高很壯,步步緊逼著,身影將外婆完全籠罩。
我撿起了那把水果刀。
他俯下身,伸出手,掐著外婆的脖子。
外婆蹬著腿,徒勞地掙扎。
我揚起了刀,狠狠刺了下去。
然而他飛快地轉過身,一把攥住我的手腕,掰開我的手指,狠狠搶過了刀。
他抬起手,扎向我的胸口。
外婆不知哪來的力氣,坐了起來,死死抱住了他的腿,張開嘴,咬了下去。
那把刀偏離了一寸,扎在了我的手臂上。
血花四濺。
鄰居叔叔咒罵一聲,一腳踢在外婆的肩膀,舉起刀猛然砍下去。
我飛快地撲過去,試圖攔住他。
那把水果刀穿過了我的手指。
扎在了外婆的脖子上。
血流如注。
外婆一瞬間睜大了眼睛。
她張開了嘴,像要說話。
她抬起手,似乎想要摸一摸我的臉頰。
但她的手才舉起來一點點,很快又無力地垂落。
劇烈的疼痛從手指漫到了我的心口,我跪在地上,拼命捂著外婆的脖子,血越流越多,從我的指縫漫出來。
止不住,血怎麼止不住。
我痛苦地嚎叫起來。
狗叫聲又連成了一片。
巨大的影子從身后投到了身前。
那道影子揚起了手,握著刀的手臂,對準了我的背心——
呼嘯的警笛聲響起。
2我又做了那個夢。
夢里回到了十七歲那年的秋天,外婆為了保護我而死。
我擦干凈眼淚,坐了起來。
手機界面還停留在百度地圖的街景。
外婆在2015年的夏天,正彎著腰,看老鄰居們下象棋。
那是外婆僅存的影像了。
這麼多年,她都沒拍過幾張照片。
我望著手機,不知不覺,眼淚又落了下來。
很燙的一滴,砸在了手機屏幕上,我伸手去擦,卻感覺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引力,拖著我,將我拉到了手機里面——
我猛然睜開眼睛。
周圍的布置卻并非2023年我的那間小公寓。
外婆曬的蕎麥枕頭、有老式肥皂香味的被子、長出一截的睡衣……
我攤開手,十指光潔而干凈,沒有那年握刀時留下的深刻疤痕。
這里是,2015年的,我和外婆的家。
鬧鐘叮鈴鈴地響了起來。
我看了一眼時間。
2015年10月17日。
外婆去世的那天……
我隔了很久才想起來要關掉鬧鐘,房門被推開。
外婆系著圍裙,笑瞇瞇的:“今天給你做了牛肉粉絲包子,快起來吧。”
陽光透過單薄的窗簾照進來,照在她的白頭發上。
見我沉默,她走了進來,先在圍裙上擦了擦手,然后摸摸我的腦袋:“怎麼了?想賴床?”
掌心的溫度,是熱的。
我張開手臂,緊緊地抱住了她。
眼淚細密而無聲,滴在了她起球了的圍裙上。
外婆一愣,輕輕拍拍我的背:“做噩夢啦?沒事兒,夢都是相反的呀。”
夢都是相反的,一定是的。
我擦干凈眼淚,去吃早餐。
熱騰騰的牛肉粉絲包子,是記憶里熟悉的味道。
“調料里都放了什麼呀?”我問。
外婆給我盛了碗粥,說:“牛肉切碎,放蔥姜水,放料油、鹽、醬油,再來上一點白胡椒粉。”
怪不得多年之后,我在廚房里嘗試再嘗試,也做不出一樣的包子。
原來……外婆的味道,是白胡椒粉啊。
熱氣熏到眼睛,我又想掉眼淚。
外婆渾然不覺,拿著湯匙攪拌我的那碗白粥,試圖讓它涼得更快一些。
“昨天居委會還發了電影票呢,可惜你不在家,也看不成。”外婆說。
我轉頭看她,有什麼破碎的靈光閃過腦海。
我慢慢說:“學校今晚搞跳蚤市場的活動,取消晚自習了。
咱們一起去看電影吧,直接在電影院碰面,可以嗎?”
外婆笑了起來:“那可太好了。晚上七點鐘,我在電影院門口等你。你想吃爆米花嗎?我給你做好了帶過去。”
望著她的笑臉,我也跟著笑起來。
盤桓在心口的那口悶氣,漸漸地散去。
時間快來不及了,我把最后一個包子叼在嘴里,匆匆穿鞋出門。
外婆小聲說:“慢點吃,沒事的,別噎著啊。”
就要關上門的那一刻,我停了下來,轉過身,抱了抱小老太太。
“外婆,你要好好的啊。”
咬著包子的聲音含糊不清,她大約沒有聽清,只是笑著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“路上慢點走啊,注意安全。”
我三步并兩步地跑下樓,在拐角處撞上了一個人。
我連聲道歉:“對不起對不起。”
她笑了起來:“言言姐姐,你也起晚了?要不要坐我爸爸的車?”
我猛然抬頭。
是樓上的那個叫做思佳的女孩兒。
而她身后,那個坐在駕駛座里的男人,正是那個把我按在車棚里的強奸犯。
此刻,他按下車窗玻璃,和藹地說:“言言,反正順路,我送你吧。”
后背起了一層冷汗。
我極力克制手指的戰栗,微笑著說:“不用了,我和同學一起。”
車子駛遠了。
我在公交站台,渾身控制不住地發抖。
3午休時,我請教班里那幾位經常溜出去上網的男生,問他們都是怎麼出校門的。
他們紛紛笑起來:“姜言,你學壞了啊。”
我有些窘迫:“麻煩你們了。”
趁著四下無人的時候,他們帶著我去操場最角落的地方。
幾個男生助跑著,撐著墻壁,輕巧地翻了出去。
隔著一堵墻,他們喊:“姜言,就這樣,翻出來,我們在外面接著你!”
我學著他們的樣子,助跑起來,然后,膝蓋撞上了墻。
手指也摳破了。
唯一一個還沒翻出去的男生蹲了下來,拍拍自己的肩膀:“踩上來。”
隔著八年光陰,我已經想不起來他叫什麼。
目光落在他的胸牌。
許宵。
見我沉默,他催促:“上來啊,你那點體重,我完全沒問題。”
他搭起兩只修長白皙的手,讓我踩上去。
接著,我踩在他像青竹一樣薄而韌的肩膀上。
他扶著我的小腿,站了起來。
我順利地坐在了墻上。
遠處忽然傳來保安的叫嚷聲:“喂,你們干嘛呢?!”
許宵往后掃了一眼,迅速起身,飛快助跑上墻,輕巧落了地,向我張開手臂。
“姜言,跳下來,別怕!”
保安的聲音越來越近,我心一橫,跳了下去。
穩穩地落入他的懷抱。
他很快松開了我,下一秒,又握住我的手腕向前飛奔:“愣著干嘛?跑啊!”
其他人都去網吧了。
只有許宵插著兜,跟在我身邊。
我走進超市,問導購有沒有防狼噴霧賣。
導購還沒說話,許宵先發話了:“有色狼跟蹤你?”
我連忙說:“沒有沒有,只是有備無患罷了。”
防狼噴霧竟然那麼貴……
149元。
我攥著手里的五十元人民幣,小心翼翼問:“我可以還價嗎?”
導購看上去有些無語:“妹妹,這里是超市,不是菜市場。”
我失落地把噴霧放回了原地。
一只手越過我,把防狼噴霧丟進了推車里。
染著紅色寸頭的少年矜持地亮出了錢包,一沓粉色的人民幣在閃閃發光。
他言簡意賅道:“小爺我有錢。你還想買什麼,一起買了。”
他有錢,我可沒錢還。
最終我只買了一瓶防狼噴霧。
我想把五十塊錢給許宵,被他推了回來。
他說:“我不想要錢。你早上吃的什麼包子,看上去好香。以后能給我帶點兒嗎?我也愛吃包子。”
我一愣:“好的。”
好的,如果我還能看見明天的太陽的話,我會這樣做的。
我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車。
許宵也跟著上來了。
我不由得發問:“你不用去上網的嗎?”
他吊兒郎當笑起來:“你不用去學習的嗎?”
我被懟得無話可說,只好側頭去看窗外的風景。
尚未拆遷的老建筑,沿街叫賣的糯米糍粑、金黃清香的桂花樹……
這些,在八年后的城市改造中,都消失了。
公交車停了下來。
我下了車,跑到站台邊,迅速鎖定了目標。
我在樹根處刨了個坑,埋下了我的鬧鐘。
鬧鐘已經設定好時間了。
今晚九點半。
上一個時空里,我被拖到車棚的時間。
鬧鐘的聲音是我的錄音:保松小區7棟樓車棚,有人殺人啦!
許宵蹲在我身邊,很疑惑:“你是在玩尋寶游戲嗎?”
我忙不迭地把土推回去,說:“嗯,我在玩一種很新的游戲。”
有小石頭砸到了鬧鐘,它突然神經質般大叫:“保松小區7棟樓車棚,有人殺人啦!”
我手忙腳亂地拎出鬧鐘,匆匆關掉。
許宵一臉嚴肅地看著我,把我看到心虛。
我緩慢開口:“那個,你聽我說……”
許宵笑嘻嘻地打斷了我:“你在玩現實版天黑請閉眼嗎?”
我松了口氣,說:“對的。”
他勾住我的脖子,笑出兩個梨渦:“帶我一個唄,姜言。”
我當然不可能帶他。
鬧鐘和防狼噴霧,是我給自己準備的雙保險。
我真正想要避開那場兇殺案的方法,是跟著大家一起去看電影、一起回小區。
這天晚自習的時候,我把幾冊書攤開放在桌子上。
又旋開了藍筆、紅筆、黑筆,裝出一副我只是出去一下下的模樣。
順便叮囑同桌:“巡邏的老師要是問起來,就說我去辦公室問老師問題了。”
晚讀的下課鈴響起。
大家三三兩兩地涌出走廊。
我小心翼翼地拎著包,貓著腰跑向操場。
好不容易跑到了墻角,書包被人猛的拉住了。
我的心跳都快停了,卻見許宵笑瞇瞇地站在我身后。
“姜言,大晚上的,干嘛去呢?”
我的手指收緊了書包,戒備地看著他:“我有事。”
他低下頭瞧著我,勾起唇,壞笑:“你該不會網戀了吧?”
我沒回答,許宵自顧自地說下去:“你這又是防狼噴霧,又是天黑請閉眼的,看來網戀對象不可靠啊。
”
說這,他慢慢蹲下去,拍了拍自己的肩膀。
我愣了:“你干嘛?”
許宵仰起頭,黑漆漆的眼睛倒映了月光,嫌棄道:“就你那小短腿,沒有我,可怎麼紅杏出墻啊?”
4許宵說教了一路,給我灌輸安全意識。
我也不反駁,由著他跟在后面。
電影院就出現在前面。
許宵聽上去很惱火:“你知道大晚上的私會男網友多恐怖嗎?你們倆還看電影?!你知不知道男人非常愛在電影院里動手動腳的!”
我終于找到了那個熟悉的身影,喊了一聲:“外婆!”
守在門口的外婆也沖我招起手。
許宵的聲音戛然而止。
我笑瞇瞇看他:“這就是我要私會的網友,恐怖嗎?”
許宵輕咳兩聲,轉移話題:“你翹課就是為了跟你外婆看電影?什麼電影,我也要看。”
外婆捧著爆米花走過來,看見了許宵:“喲,這是言言的同學吧?你也不去參加那個跳蚤市場呀?”
許宵說:“啊?什麼跳蚤市……”
我踩了他一腳。
他嘴角抽動一下,不動聲色地撤回了腳,點頭說:“對,我不參加,我來看電影。”
外婆也跟著笑了:“這麼巧?你看哪部?”
許宵乖巧回答:“姜言看哪部,我就看哪部。”
其實他根本沒票。
不知道他是怎麼渾水摸魚進來的,總之等我和外婆找到座位的時候,發現這廝已經坐在了我身邊的位置。
看見我,他還裝模作樣地微笑:“好巧哦姜言。”
我扯了扯嘴角:“聽說男人很愛在電影院里動手動腳,你離我遠一點。”
這位身高一米八的英俊少年,立刻嬌羞地抱住了我的胳膊:“討厭,人家是女生啦。”
……
電影很好看。
科幻巨制,場景恢弘,不時引發觀眾們的陣陣驚呼。
我坐在底下,卻無法融入其中,神經質地去看我的手表。
咔嚓,咔嚓,咔嚓。
幾乎難以察覺的秒針分毫轉動,時間終于指向了九點半。
此刻,鬧鐘應該在公交站台喋喋不休了起來,大概會有保安去車棚里看一眼。
那里應該一片安靜,沒有我,沒有強奸犯,也沒有血流如注的外婆。
狂跳的心終于平靜了下來,我抬頭,今晚第一次認真地看向熒幕,跟著觀眾一起鼓起了掌。
散場了。
外婆把爆米花遞給我:“你問問你同學吃不吃。”
我說:“他不吃。”
許宵說:“我吃。”
他就這麼順理成章地從我手里拿走了爆米花:“姜言,你能不能跟你外婆學學,忒小氣了。還是外婆好,謝謝外婆。”
許宵捧著爆米花回家了。
分別時,外婆還說:“以后常來家里玩啊!”
許宵嬉皮笑臉道:“您做的爆米花真好吃,下回我能吃包子嗎?”
我踹他一腳:“快滾!”
理著酒紅色寸頭的少年委委屈屈:“外婆,你看她!”
外婆笑瞇瞇:“言言可壞了,是不是?”
許宵一溜煙地滾了,臨走時嚷著:“是啊,您可要好好管教她!”
外婆牽著我的手坐上了公交車。
這一班車里都是鄰居,在興奮地聊著劇情。
外婆一向愛湊熱鬧,此刻卻沒參與對話,只是笑著看我:“剛才的那個小男孩,是不是喜歡你啊?”
我下意識反駁:“不可能,他就是貪玩罷了。”
外婆摸了摸我的發頂,笑道:“如果真的喜歡,也很好啊。這樣,世上就多一個人愛我們言言了。”
我愣住。
她明明是這個時空的外婆,卻仿佛看見了上個時空中2023年的姜言。
孤身一人居住在小公寓里,沒有朋友,沒有愛人,沒有親人。
過著殉道一般自虐的生活。
然后,這個時空,2015年的外婆說,希望多一個人愛我。
那種淚意又涌上來。
我往下坐了點,側過身,抱住外婆的腰,喃喃:“外婆,我有你就夠了。”
5公交車到站的時候,我往樹根處瞥了一眼。
那只鬧鐘果然不見了。
大概確實是響過,然后被忍無可忍的路人挖出來按了關閉鍵。
我給自己上的保險并沒有發揮作用,這其實是一件好事。
十點半,我洗漱完,回到房間。
夜色濃郁,四周一片寂靜。
我熄滅了台燈,鉆進被窩。
被子上有熟悉的老式肥皂的香味。
是最便宜的雕牌肥皂,在2015年的秋天,一塊五一只。
外婆總是帶著肥皂和板刷,去小區外的河里清洗床單被套。
水流嘩啦啦,很快地就能沖干凈泡沫。
然后在陽光燦爛的天氣里,把我印著跳跳虎的床單曬在陽台上。
粉色的跳跳虎一蹦一跳的,在風中搖晃出皂莢的香味……
我慢慢陷入了夢境。
輕微的咔嚓聲響起來的時候,我條件反射地睜開了眼睛。
用了許多年的老式防盜門發出嘎吱的聲響,在黑夜中并不清晰,卻讓我汗毛倒豎。
我下意識反鎖了門,試圖跳窗逃走。
卻猛然驚醒——
這里不是我的單身公寓,這是我和外婆的家。
外婆還睡在隔壁。
門外有腳步聲在靠近。
有人在旋我的房門把手。
但是,門反鎖了。
我半跪在床頭柜邊,快速地按下110。
“嘟——嘟——”
只是幾秒鐘,竟像是一個世紀那麼漫長。
“喂您好,110接警台。”
我小聲而急促地說:“保松小區7棟1單元301,有人入室搶劫……”
同一時間,針孔捅鎖的聲音響起,門霍然洞開!
月光照在他的臉上,我再一次看見了那張熟悉的臉。
樓上的叔叔。
那個殺人犯。
一瞬間的冰冷從腳底躥上了天靈蓋。
到底是哪里出了錯……為什麼,他又來了。
他似乎沒想到我醒著,在門口僵持了片刻。
我撲到書桌邊,哆嗦著從敞開的書包里拿出防狼噴霧,擰開蓋子,對準他。
不能讓外婆知道,不能讓外婆醒來,不能讓她在我的懷里死去。
我把所有尖叫都咽在了喉嚨里,哆嗦著舉起瓶子,低聲威脅他:“你現在走,我可以當作什麼都沒看到。”
男人只思考了一秒鐘,然后朝我沖了過來。
我毫不猶豫地按下噴霧,辣眼的氣霧噴涌而出。
男人捂住了眼睛,像是被激怒了,大手沖我伸來,我一腳踹在椅子上,椅子把他往后推了幾步。
在黑夜里發出了摩擦地板的刺耳聲響。
我聽見外婆喊我的名字:“言言,怎麼啦?”
她醒了。
我沒有回答,她趿拉著拖鞋向我房間走來。
不,不可以,不要過來!
我努力壓抑聲音中的異樣,說:“外婆,我沒事,你回去睡。”
外婆的聲音漸漸遠去:“哦,好的。”
心臟劇烈跳動,我不停地按動著噴霧,同時把一切夠得著的東西抄男人臉上扔去。
然而下一刻,房門再度被推開,外婆撳亮了燈。
她手里拿著一把菜刀。

